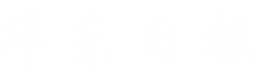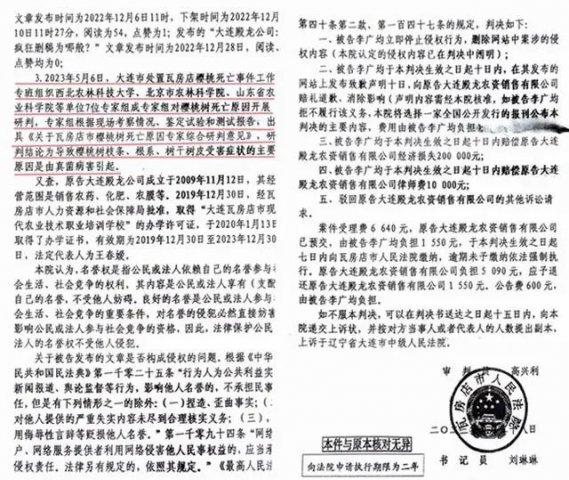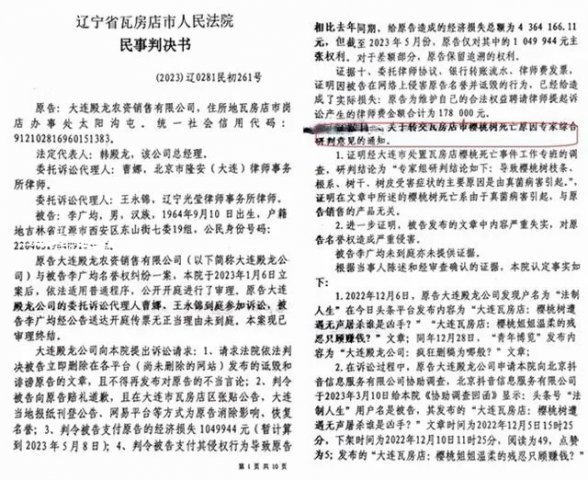他们常常诉说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(2)
2017-07-26 02:52 来源:华东日报 作者:张謇
初高中时期由于外表肖似女孩,且性格温柔,阿飞和女孩走的比较近,那时也有两个女孩格外青睐阿飞。但身体尚未发育的阿飞,心智也尚未成熟,心里也没有少男少女的懵懂之情。直到治疗之后,身体发生变化,阿飞才慢慢
初高中时期由于外表肖似女孩,且性格温柔,阿飞和女孩走的比较近,那时也有两个女孩格外青睐阿飞。但身体尚未发育的阿飞,心智也尚未成熟,心里也没有少男少女的懵懂之情。直到治疗之后,身体发生变化,阿飞才慢慢开始感受到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别。
2013年,阿飞有了第一次性经历,也结识了自己的女友。在和许多公益人士的聊天过程中,阿飞开始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,他不再嫌弃自己那有一条长长疤痕、略显女气的躯体,性之于他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但于阿发而言,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2005年的时候阿发去做了隐睾手术,手术成功,睾丸下降到了阴囊。但直到28岁,阿发都没有性欲,尽管一直都知道男女之事,但他耻于和别人谈论这些,也没有什么女孩看上略显畏缩、小心翼翼的阿发。
直到2010年,有女孩向阿发示好,阿发才决定去治疗,这一次,阿发被确诊为卡尔曼氏综合征,和阿飞一样进行促性腺激素治疗。
治疗之后,阿发的身体开始发育,心里也像长了草般渴望恋爱。有一段时间,阿发疯狂的在网上找人聊天,同一个工厂的工友,不认识的陌生人,阿发都报以极高的热情。有好几次,几乎就成功了,但最后阿发依然打了退堂鼓。他有些胆怯,胆怯别人知道自己患有卡尔曼氏综合征,更胆怯的是,怕在别人面前“不行”。
病友谈“性”色变
2012年,因为想给更多的患者以支持,阿飞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,通过微信群和QQ群交流,阿飞和病友们一起召开病友大会,联系广州、北京的医院进行义诊,在微信上做讲座普及推广卡尔曼氏综合征及性教育。
阿飞发现,即使许多人经过治疗有性能力和建立家庭的能力,他们依然对性抱着恐惧,甚至很多患者过了三十岁依然不知道什么是避孕套,没有过性经历。“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很多人害怕去接触异性,害怕别人嘲笑他们。”
对性和不能生育的恐惧是卡尔曼氏综合征患者常见的心理特征,甚至还有人因此抑郁。更为严重的是,患者家庭也因此排斥患者。
阿飞记得,有一个河南的老师,因为患此病家庭对他无比排斥,在理应结婚生子的年龄家里也无人为他张罗,与之相反的家里早早的就给其兄弟安排好了结婚事项,阿飞记得这个老师的悲怆。
卡尔曼氏综合征患者经治疗后生育率也并不高,这成为很多人的梦靥。即使治疗后有生育能力的,依然会有因伴侣担忧遗传到下一代而被抛弃的患者。
2016年,一位女病友被要求堕胎,只因丈夫发现其患有卡尔曼氏综合征,害怕遗传到一代,遂以离婚为威胁要求其堕胎,最后,胎堕了,婚也离了。阿飞听说之后无比的痛心,因为卡尔曼氏综合征不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,即使遗传了,现在的医疗技术也可以在早期就做较好的治疗。
和自身的缺陷和平共处
在阿飞的公益组织的微信群和QQ群里,有不少的家长,他们常常诉说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,被人排挤,这让阿飞想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比他幸运的是,这些孩子早早的确诊,他们无疑也会得到更好的治疗。
而更多的人,则像阿飞一样,被告知“你只是比别人长得慢了一点”“有的孩子就是迟一点发育的”,导致他们在别人的青春期结束时才发现自己身体的不对劲。有感于此,确诊之后,阿飞开始频繁的跑医院,尽管从前他最恐惧去医院。
每到一个医院,阿飞都会到耳鼻喉科、泌尿科、男科和医生聊天,他会把准备好的资料给医生看,告诉不了解的医生什么是卡尔曼氏综合征,避免误诊。
2014年,因药厂成本问题,性激素HCG停产,为了呼吁继续生产该药物,阿飞组织了一场徒步中国的活动,他和志愿者们一起分别从葫芦岛、乌兰察布、多伦,步行数百公里前往北京。这场活动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HCG继续生产。
如今,阿飞和志愿者们依然坚持徒步活动,他们不再坚持什么主张,只是每路过一个医院阿飞依然要去“科普”一下卡尔曼氏综合征和其他罕见病。在外人眼中,阿飞俨然已是卡尔曼氏综合征的代言人。
同许多选择隐瞒病情的病友相比,阿飞并不抗拒自己身上被贴上“卡尔曼氏综合征患者”的标签,也不怎么介意别人暗暗的揣测和异样的眼光。多年的治病生涯,已让他学会和自身的缺陷和平共处。阿飞的家庭也很支持,提及家庭他一脸得意,“他们都觉得我在做好事,这就够了。”
阿飞记得在徒步过程中,自己遇到过无数暖心的人和事。一次徒步经过唐山时遇到一个卖西瓜的大叔,大叔听说他们的故事后坚持每天都在微信里给他们发红包,次年再次经过唐山时,阿飞听闻,大叔自己开设了一个公益组织。
阿飞觉得有些感动,“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改变了一些人,让公益的力量更加壮阔。”尽管时常面对别人的不理解,但因这点点滴滴的感动,阿飞决心将公益继续做下去。
文: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诗蓝
图:由受访者提供
看图
热点内容
- 2025-06-24
- 2025-10-13
- 2025-11-17
- 2024-09-26
- 2024-05-30
- 2024-09-29
- 2024-06-29
- 2024-08-30
- 2024-04-17
- 2024-07-17